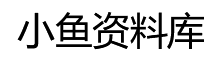沉重的肉身读后感
篇一:沉重的肉身读后感
读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中题为《沉重的肉身》的那一篇。喜欢刘小枫特有的,用于哲学散文的湿润的文笔。那种需要逐字去领会,推敲其中逻辑推理和品味文字迂回曲折的阅读感觉,是与读亦舒小说的畅快淋漓完全不同的。慢慢地看,有些地方还需要反复地跳回去重新解读,这种凝滞的感觉就像拉长了的盛宴,每一次咀嚼都有完全新鲜的味觉享受。
《沉重的肉身》谈到关于男人对女人选择的性伦理,谈到身体和灵魂感觉的地位对比,以及个体差异等等。文中反复提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及这个故事的源头故事——“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坐在十字路口,面对着两个女人:卡吉娅和阿蕾特。卡吉娅能给男人带来的是性和生活的逸乐,代表着生命之轻;而阿蕾特带来的是辛劳厚重的身体感觉和生活经历,她引导男人通向生命之重——所谓的“美好”。赫拉克勒斯在这两个女人之间的选择代表着男人对于不同生活、不同伦理的选择。这个论题被男人们唠叨了数千年,发展到昆德拉的版本,就变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萨宾娜和特丽莎的故事。在刘小枫的解读中,昆德拉似乎还增加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中“人民-意志”的因素,将男人的性漂泊由寻求女人身体感觉的不同以及背后隐藏的生命意义的不同,进一步演绎成探求历史规律下趋同群体中个体的差异。似乎托马斯的行为写进
三流色情小说中不过是拙劣的风流韵事,而经过哲学化的处理就变成了对历史和社会的政治性反抗……这些逻辑让我感觉极其可爱,是我看到的对于男人动物性的滥情的最新鲜也最富丽堂皇的解释。
不过话说回来,最后文章里谈到了托马斯的选择,或者说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或者说是昆德拉心目中男性群体的选择。托马斯的性漂泊终于止于特丽莎:他在一个又一个女人的身体之间游荡,寻找每个女人身体中那百万分之一的差异,而最后,他发现了特丽莎与所有个体的不同——这是一个他愿意与之共眠的女人,而且他的灵魂开始排斥特丽莎以外的女人的身体……这里文章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关于差异的个体。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化了。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说明不过就是他爱上她了——在他阅过无数个差异的个体之后,他找到了一个拥有自己最在意的特点的那个个体。当然如果文章里说得像我的语言这样直白和浅薄,大概就该放上言情小说货架了,不过我还是愿意用我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昆德拉的原著,多少有些感性的意味,少了些理性的分析。
篇二:
讲故事是人类自我发现的一种方式。刘小枫说,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到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人们发现生活混乱不堪时。当一个人的生活遭遇挫折或不幸时,叙事能让人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生活中无暇发现的自我。人类的起源,似乎是从劳动开始的。但人的生活感觉,似乎是从讲故事开始的。
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讲述了叙述的伦理构想。生命的感觉来源于每一个个体的体验,因此,每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伦理探讨个体生命的意义,然后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叙事改变了生命的感觉,无论是听故事或讲故事的人,都曾经在讲述中改变事件本身的态度。于是生命感觉发生了变化,伦理产生了道德实践的力量。
阅读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仿佛踏入现化伦理学的深渊,在破碎的叙事片段中反复叩问。
萨宾娜像一个沉重的幽灵,出现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刘小枫把萨宾娜的身体暂且形容为“妓女玛丽昂”的再生。通往萨宾娜身体的感觉是反意识形态的。而特丽莎的身体则表征了“美好”。托马斯对生命感觉产生的疑惑,使他对两位女士的身体作出了两难选择。在电影《布拉格之春》里,托马斯像个三级片演员,把肉体的迷恋表现得丝丝入扣。但《沉重的肉身》提出了问题:身体感觉的差异来自灵魂还是身体?
没有差别的身体等于没有自己的生命时间。灵魂才使身体有超出身体局限的感受能力。托马斯与萨宾娜有相同的生理反感。在那些报纸头条所编织出来的道德理想主义言论中,他们都看到了最大的“媚俗”。
卡夫卡似乎是拒绝身体的。当他即将与菲莉斯小姐走进婚姻殿堂时,他想到的是,在夜深人静时,他是否需要跟一个女人睡在一起,还是独自一人看书。卡夫卡想通过婚姻来摆脱父亲的阴影。但他又害怕给自己带来的负罪感。摇晃在灵魂钢丝索上的卡夫卡,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对自己进行追问。是面对自己还是隐藏?对于卡夫卡来说,他追问得越多似乎就越发现自己的罪:自私、虚荣、怯懦……
结婚当然是一对男女从灵魂上互相认识,但卡夫卡对这种认识充满了绝望。刘小枫把卡夫卡的生命感觉总结为“一片秋天干枯的树叶”。这片干枯的树叶也追求过幸福的阳光,但最终还是希望以自我审判的方式重返天堂。
薇娥丽卡很幸运。她有两个身体。斯基洛夫斯基的《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中,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与巴黎的薇娥丽卡互为灵魂。为什么呢?难道生命感觉可以一分为二吗?刘小枫说,是的,一个人的生命具有各种生活的可能性,慈悲的上帝不会来过问这个身体的偶然遭遇,只对个体遭遇中的生命意味抱以关注。薇娥丽卡从另一个薇娥丽卡身上体验到我在感。不管是热情、快乐还是死亡。当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身体死亡之时,巴黎的薇娥丽卡也感觉到了尖锐的伤心。
难道这就是死感吗?当灵魂感觉到身体之死时,当作何感受?身体与灵魂分离的薇娥丽卡总在寻找生命的感觉。她热爱唱歌,她的所有热情都是为唱歌而生的。薇娥丽卡的生命中交识着性感、死感和哀歌,但没有一个人能懂得她的灵魂。
似乎总在讲故事。故事激发了每个人的生命想象空间,并探讨叙事观望到的个体生命的伦理深渊。每个人都可以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依从自己的道德自律做出生命中的各种选择。
篇三:信仰的羁绊——《沉重的肉身》读后感
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是一本关于现代性伦理的文集,初看书名我设想书籍内容关于“身体的罪恶”“肉体与灵魂”的书籍,舍友猜疑是一本性的书籍,也有人将其解读为理想与现实大作,阅读下来,对于书籍的构想也纷繁复杂,既像政治,阐发人民民主与自由民主、个体与群体之悖;又像是谈生活,抛出社会道德与个体本性、守欲与纵欲之争的话题;也像宗教,进而将读者引进人义与神义、自我抉择与上帝杠杆的伦理困境。最后,我不得不摒弃挺不愿意接受但现在不得不接受的观念,(我想我应该是作者笔下那个耻于谈性,守群众之规抑个体之欲的人)这到底是一本讲性的书。
肉身很沉重,为何?人民公意中,身体的自然受伤被转移到应然的法庭来重新评理,故沉重;对象的选择上,“你应该与阿雷特在一起”,将轻逸冠之以邪恶,只为了让生活趋近真切与实在,名曰美德却沉重。而实际上,任何感觉都没有在道德意义上高于其他感觉的权利,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感觉都在伦理价值上都是平等的,生命显得轻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丹东为玛丽昂正名,尼采顶撞了苏格拉底,人民伦理也顺应时代而转至自由个体伦理。
但肉身还是很沉重,为何?肉身浑身是偶然,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故沉重;个体自由的社会增加了无法解决的偶然的身体造化的欠缺,个体幸福偶在性增长,导致个体在世负担;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被理性化世界设想和实证性生命勾销后,个体自己身体的死须由自己身体单独承担,造成个体灵魂的在世重负;小说家呵护现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的叙事本身,讲述生活伦理,负担沉重;选择自由伦理,而其艰难让身体伤痕累累,故亦沉重。
这到底是一本讲性的书?我想不全是吧。但至少读毕此书,我对这个观念接受了不少。我妄自猜想书中大概想涤荡我们的信仰,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可最终我们信什么呢?这是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可作者也没有一个标准。
一本好书,是否应该奉之为一生的信仰加以追捧?书中却说不要偏信唯一——标准。
书中说“‘唯一真理’”的哲学会引出专制社会,‘唯一道德’的伦理学会导致专制道德……”,想想也就接受了,的确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可还是不由自主地想问自己此书我该信什么?
作者在序中所说的文字艰涩难懂,其实也没有,反而是将前人文学和历史事件呢喃道来,叙事与论理铺成展开,倒是最终的还是陷入了没有标准的世界。虽将世间伦理悖论分条缕析,将两种不同的个体自由伦理陈显,捧到读者跟前,这是大师的两种信仰与困境。
“昆德拉人义论自由伦理承认自身的欠缺,肉身的偶然存在,但乐于在自身的欠缺中沉醉,在既不知生又不知死的生存迷雾中找寻和选择兴奋的瞬间。”
“基斯洛夫斯基神义论自由伦理承认自由伦理是艰难的,而且是欠然的自由,即便具有这既艰难又欠然选择自由的人,也无从推开自己的自由选择的道德承负。基斯洛夫斯基搂抱如履薄冰的生存者。”
我觉得被刘小枫带着兜了一大圈,说大家不要相信群体神义,遵从个体人义,最后又提及人义是欠然的,大家还是投入神义的怀抱。人义和神义,这是两种信仰,可标准呢?作者避而不答。
没有标准,大抵因为从人民公意转至自由个体伦理,社会中个人的作用在一瞬间凸显,我不管社会,只管自我张扬。大概可以套用那句老掉牙的话“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所以你不该强求一,因为人民公意的社会已经不再了。地球上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就不应该有一个标准,而该个体、个性化。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的现代社会,可没有标准,过得很累。太杂太乱了,可惜偏偏是个体自由,乱作乱有理。东有理,西有理,放在策划上就是策划者眼里一切东西都是原材料,放在经济上就是一切东西都可以拿来卖,大家的价值观念放平了,没有所谓的良莠,一切都是歌舞升平,可实际上,个体的呼声愈发强烈,良和莠渐变地获得同等的价值之后,其实这个社会变得异常地糟糕。个体自由后,人与世界的关系越发地变少而清晰,为何?功利性越发地强烈,只因为这世界没有一个标准,与世界联系的唯一标准,让这世界不要太过功利。
顾彬说,我最讨厌现代主义,它没有标准。我还有信仰,我还完全相信传统。我觉得现代性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到了现代性以后,我们什么都丢了,没有什么基础,所以什么都是暧昧的……原来是一个皇帝,一个上帝,我们听他们的,现在没有了,我们要自己决定,你能决定吗?……20世纪发生了群众现象。群众最怕的是作为个人。但是现代性要求的是你要成为个人。
顾彬和刘小枫,我觉得同是在讲这个社会的发展现象。个体自由被呼出来后,基斯洛夫斯基看到了它的欠然,投入了神义的怀抱。顾彬觉得它是个错误。作为个人,我总觉得很简单而自然而然,请给我个接受的标准。
为什么要一个标准,因为本来是有个信仰的,书籍让我摒弃原有共有信仰,让我投入个体信仰,可这个世界的信仰太过纷繁复杂,就找不到自己的信仰了。从一个黑洞中拉出来,满心欢喜,却堕入另外一个黑洞。
我知道,强求书籍给出一个标准或许是可笑的,这或许本身就是个悖论的东西。可没有个标准毕竟不是好事,你可以说我这是叫功利性读书,我可不想对着悖论使劲兜圈,这是种原地踏步的行为。给我个信仰的标准,好让我笔直地走下去。
篇四:《沉重的肉身》读后感
说它是文学书,是因为当我非常想写点读后感时,发现它竟是难以用思辩的语言来评判的。某种程度上,它还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那些还可以用思辩的语言分析,而它的不可评判却带着诗性。不管我同不同意文中的观点,(其中有些源于信仰的差异,我的确不同意),它的诗性都使得它无可辩驳。如小枫自己(在别处)所说,这是生活的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我读小枫的东西是从怕开始的,一直在战栗中前进。也许习惯于黑暗的温顺的人难以适应突然见到太阳的刺眼,他那么毫不留情地点破真理,我时常觉得吃不消。直到这本书,我才看到那与怕对立的爱。小枫的爱是基督徒式的,自然与尼采是相反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一种奇特的相似。柔弱的人生要直面命运――尼采所要直面的那个必然和小枫要直面的那个偶然,其实是吊在同一个深渊上的绳子。他们同样睁大眼看着,同样咬着牙攀着。同一根绳子上的兄弟,同一个深渊上的两个诗人,向上看到不同的解救之像,但向下看到的是同一个深渊。
小枫的选题和行文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他精心安排自己的文字乃至篇章的排列,他所选取的叙述方式当然也不是兴之所致。叙事的言语是为了表达思辩的言语所不能表达,虽然所要表达的竟是思想!仅仅是方式的选取已传达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思想本身无法脱离个体的生命感受而轻逸地独存。于是小枫用文学言哲学所不能。
关注个体的生命感受,首先就得关注肉体。“Seele ist nur ein Wort für etwas am Leibe.”(查拉图斯特拉:“灵魂只是关于身体的一个词语”)想必在惊动了如我般后现代众生的同时也曾(也许仍然)深深惊动小枫。基于对Leibe的普遍理解,即纯粹的物理性的“肉体”,自由主义伦理分裂了。人义论者义无反顾地沿着他们所以为尼采所指明的大道去了,而神义论者却背对尼采向古代张望,希望找回被尼采一笔勾销的灵魂。可是现代之后,每个人都惶惑,以昆德拉为代表的人义论者因大道渐渐展宽为茫茫荒野,突然发现不知何去何从,以基斯洛夫斯基为代表的神义论者却因不能找到精神故国,空具一副渴望灵魂的躯壳。
小枫没有过分追究尼采本人,因为尼采其实在悬崖边缘顽强地站住了,他只是把我们这些糊涂的后人(误?)推下深渊。尼采这个其实最爱灵魂的人偏偏要用Leibe来表达他的灵肉统一观念,也许是个出于反叛的相当痛苦的抉择。当他满怀憧憬地回想那些“经过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美丽”的希腊人如何“勇敢地停留在表面时”,他绝不可能真的相信那些美丽的身体仅仅是物理的原子分子细胞组织偶然的低级的叠加,否则他个人的生活也不会那样禁欲。而小枫开始反叛尼采了,从那难以名状的etwas开始。
尼采对灵魂的反叛是出于对它的热爱,因为与肉体的长期分离已使它形容枯槁,成为真正的游魂,任权威伦理评判的雷电风暴随意劈打。而同样,小枫对肉体的反叛是出于对肉体的热爱,因为他不堪忍受肉体在它“自在性”的现代谎言下烂为一具腐尸。他要恢复肉体的神性,肉体独一无二的尊严,尽管他回归神性的道路这样古老荫庇,太古老太荫庇,已经路径不清。
相关文章: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