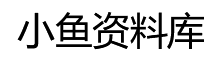人到中年,才知道当独生子女有多苦逼
人到中年,才知道当独生子女有多苦逼
文/刘黎平
我算是七零后中的奇葩,1971年出生的,居然是独生子,是父母提前响应国家的号召?对于国家号召这玩意,有个网友说得好,只要你不去响应它,迟早会有好处的。
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都生了七个八个,平凡如我父母,当然不会如此先知先觉,之所以生我一个,时也势也。
我老爹年轻时是新华书店员工,因为受姑父被打成右派的牵连,下放农村;我老娘是知识青年,没想到去响应老人家的号召,被动地下放了。
不知道是谁喷的,说人越少,人均资源就越多,生活水平就越高,你看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地广人稀,富得流油,我就纳闷了,我出生那会,中国人口才不过九亿,真***的那个穷啊,我爷娘所在的生产队每到过年,每家每户过年发的过年物资也就半个橘饼,五六颗红枣。
橘饼每户只能发半个,于是拿把菜刀切,每户切一半,这可是个技术活,切得不均匀,两家还要打架。当地人姓毛的多,有一回有人切得不好,切饼的人发怒:“嫌老子切得不好,你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切啊。”
其实,家乡土也肥沃,种什么长什么,水也甜美,地下还能刨出大把煤炭,当时人也不多,但这样好的配备只有一个结果:穷。
一年的口粮有三分之一是地瓜,生产队每人每年四百斤谷子,而且还未脱粒,湿湿的。要挑到水电站去打谷脱粒,水电站的打谷机时好时坏,时停时转,打几十斤谷子要等老半天。哎,那个穷啊。
大约是我四岁那年吧,记得父母和姑父姑妈带我上街,我看见一家商店的玻璃坛子里有一个饱满鲜红的果子,我不知道是啥,但我知道它好吃,于是闹着要吃,爷娘买不起,只好无视我的要求,幸亏姑父是国家干部,掏钱买了一个,我一口咬下去,又甜又鲜,我抬头看着县电影院墙壁上的毛主席像,他老人家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觉得好幸福啊。
那天,我才知道那个果子的学名:苹果。
我六岁以前,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穷得没有任何希望。因此爷娘商量好了:就生我一个。再多生大家连带受苦。若干年前有记者说越穷越生,瞧那种高高在上做道德判断的优越姿态!我真想撕他嘴,怎么喷的你?
四人帮垮台,一声春雷,父母回城了,父亲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母亲安排在县五金交电化公司,生活顿时两重天,条件好了,爷娘想生第二胎,然而,国家计生政策趋硬:只能生一胎,否则回乡下种地。
那时城乡生活水平区别特别大,穷怕了的父母,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于是母亲结扎,领了独生子女证,我欢欢喜喜做我的独生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城市独生子,确实很幸福,这一点我不能否认。
那时候五金交电化似乎是天下最牛掰的公司,县法院院长为了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上门来求爷爷告奶奶,居然连五金公司经理的面都见不着。公司每年夏季会给员工发放大量的防暑水果,尤其是西瓜,每个夏季都会堆满我家的床底。
我是独生子,没人跟我争,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花样百出,就差煮熟了吃。
而隔壁彭叔叔家有三个孩子,为了争吃最好的西瓜,老大老二两个男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打得西瓜满地乱转。
老三是妹妹,抢不到,坐在地上娇滴滴地哭,两个哥哥也不知道心疼她。也许是西瓜吃得少,这妹子后来出落得如花似玉,在县比美大赛中进入十佳,再后来嫁到台北的大户人家当少奶奶。
城市的独生子,意味着物资不存在所谓的配给,父母拿回来的给孩子的福利,都是你一个人的。
我在同辈人羡慕的眼光中长大,从红孩子班(那时的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有一个绰号相随始终:“独生子”,其含义其实和现在的奇葩差不多。
殊不知,早年的享受也是要后来买单的,生活从来都是收支平衡,你享受独生子女的幸福,就得担当后来的应有的责任。
独生子女远离父母工作,其实风险蛮大的,而我就犯了这个风险,我一直不知道我舍弃父母之邦,把父母扔在故乡,南下广州重新开始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我太自私,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现在想起来都犯迷糊。
2005年,父亲查出大病,都已经是晚期了,必须得手术。按就近照顾原则,最好当然是接到广州来看病开刀,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料父亲,两不误。
然而,按照经济的原则而言则不然,爹的公费医疗在湖南才有效,对于我们这样的中低层收入者而言,这一层因素是百分百要考虑的。
生死大事,固然不能以省钱为第一,但也不能多花冤枉钱。
这样权衡下来的结果就是:我请假回湖南,将父亲挪到长沙去住院动手术。长沙虽然是家乡湖南的城市,其实这只是一个大范围概念而已,从空间距离而言,根本就不算是家乡,父母之邦双峰县距长沙两百多公里,衣食之地广州距长沙六百多公里,长沙根本就是一异乡。
身在异乡,我当时的心,惶惶如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有点啃老心态,买了房,还想着从老人家那里弄点装修费,爹却一不小心就老了,衰了,病了,病体侵蚀他的肌体,黑瘦,枯黄,憔悴,想着当年他和母亲把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全都抛给我,让我独自尽情享受,如今,吃了的西瓜转化为责任,甜蜜转化为苦涩和艰辛,儿呀儿,你得担起责任了。
慌慌张张叫了一辆县医院的救护车,六百多元,到了长沙,不敢跟两个老人家说,怕他们心疼我的钱,我当时还在供房,说熟人照顾,只花了三百元,说得老人家欢喜起来,说熟人真好。
到长沙,将老爹送入一家专门医院,正是深秋季节,落叶瑟瑟,老爹住院,我和老娘、老婆租那种每晚十元租金的民居,真闹不清山清水秀的湖南怎么这么多病人,医院外面供病人家属租住的房间遍地开花,租屋外面的湖面上浮满泡沫垃圾,秋风一扫,臭不可闻,就在窗外。
本来人手紧巴巴的,老婆上班的学校,白云区一所中学,校长来电话,催她回去上班,老婆说家公要动手术,校长说家公又不是直系家属,你忙什么忙,否则就按事假扣钱。
正在供房的我家怎敢轻易被扣钱,于是老婆第二天就买站票回广州。
这个校长也是湖南人,学音乐的,真闹不清,我到广州以后,最喜欢我过不去的几个人基本上是湖南人,尤其是湖南女人。老爹在广州检查身体之前,我心里正七上八下,没想到在办公室被一个湖南衡阳籍的女领导骂得狗血淋头,当着几个办公室的人骂,忍得我好辛苦,好辛苦。
后来陪老爹去看一个专科医生,碰上开会,我硬着头皮发短信请假,该女领导恶意地将一场会议分成上下两场,只答应给我上半场的假,这待在广州的个别湖南女人还是人吗?
天可怜见,当时的大领导,也是女性,广州人,却宅心仁厚,说我回去是尽孝是天经地义的,快回去吧,莫担心这里的工作,我的眼泪没有在眼眶里流,却在心里头流淌,感叹万千地回了湖南。若不是她保护,我估计在不被老乡迫害致死,也迫害致残了。
还是说回老爹的事吧,老婆回广州了,我真的有点慌,不对,不是有点慌,而是很慌很慌。
跑医生那里问老爹病情,每听一次,心情就慌一次,没有任何消息,但对着老爹,又得强颜欢笑:“没事呢,医生说。”慌!
又得去跑市场,买米买菜,娘也老了,很怕她老人家在长沙走丢了,娘在年轻时跟着老爹跑来跑去,现在年老了,只能跟着我跑来跑去,而我当时完全没有主意。慌!
幸亏当时有一个发小在该医院实习,总算能拉上开刀的医生吃个饭,套套近乎。
老爹手术还顺利,尽管带了止痛棒,但晚上还是痛得厉害,哼哼地不能安睡,老娘和我不停地抚摸他,徒劳地给他止痛。老娘心疼我,要我早点睡,老爹哼着,哪里敢睡。
直到下半夜,才去病房凉台上睡着,老娘却还没合眼,远处黑魆魆的岳麓山上凉风透过防盗网栏杆吹来,梦里凉凉的,心里头忽然冒出一个概念:弟妹。
有个弟妹可真好,大家可以轮流着来孝顺,大家都有觉睡,父亲床头也不缺人照顾。
在湖南耽搁了这么久,得急着回去上班了,大领导虽然好,同事们也好,但按揭这事儿半点马虎都来不得,再超过假期就得请事假了,但老爹的出院手术咋办?
没有弟弟,幸亏还有个表弟,在长沙工作。表弟也是弟啊,这时候真庆幸老娘并不是独生女,还有姐弟,还有外甥,我还有表弟。
表弟答应帮老爹办出院手续,并送老爹老娘去车站,我千感激万地离开长沙。
在坐车去长沙火车站的路上,忽然掉眼泪,简直是爆眼泪,一直哭到火车上,火车又载着我的眼泪,一路到广州。
想起父亲的病,那位当医生的发小说,最担心复发,想起老娘的辛劳,我当初离开湖南到底对不对?
如果有个弟妹在身边,哪怕要我去安慰他或者她,也会好一点吧,安慰兄弟姐妹,其实也是安慰自己,大家取暖,人皆有兄弟,何我独无?
2007年,父亲的病又复发,当时他在广州和母亲一起给我带小孩,他闹着要带孙儿一起睡,因为怕空调让小孩受凉,他反正睡得警醒,可以给孙儿扇扇子,用他的话来说是葵扇的“微微风”可以不让小孩受凉。
偏偏这个时候,他的病复发了,疼痛,尿道不通,进了某家军医院。一天到晚痛,医生也不管,那家医院的空调开得特别大,凉飕飕的,这让父亲更疼痛了。
我急着找熟人,看能不能对父亲积极一点,找不到,母亲很着急:“你老爸痛着,你想想办法呀。”我也着急,可有什么办法呢?上天入地找不到熟人,对父亲的惨状,医生的反应是,连个普通的指检都很吝啬得不肯出手。
我没辙了,我只好在医院走廊里悲愤地大吼:“你们领导呢,你们主治医生呢,都死了吗?都给我出来。”
吼声惊动大楼,主治医生很生气,和我怒目相对,我也豁出去了,瞪着他,捏着拳头,他总算心软了,主动给我父亲做检查,但最终不了了之,一直没弄清楚老人家疼痛的原因。只能断定:复发。
广州这里是没辙了,赶紧回湖南,去长沙,有家百年老医院,还可以有办法。
当时儿子还才一岁多一点,老爹老娘和我回湖南,儿子没人带,老婆只好带着他第二天晚上回湖南娘家,那里还有外婆外公。
真可谓劳燕分飞,我带着父母跑火车站,老爹一手还得牵着自己的身上导尿管,和正常人一样,一路长跑步找车厢,跑得气喘吁吁。
后来老婆告诉我,她也狼狈不堪,虽然是卧铺,但每次上厕所,怕儿子被人抱走,都得抱在身上,尤其是蹲下来的时候,好不辛苦。
在长沙,暂时没有铺位,只好一家三口在走廊上睡着,白天热得不行,那日头淋下来如同开水,树叶都烫得白花花的。走廊上拥挤,我只好花两元钱一个小时去网吧补觉。
父亲做了很多检查,核磁共振,PTCT,等等,要承认,这家老医院的医生负责多了,最后大致确认:病在腹部复发。
拿着父亲的诊断书,我在走廊上急得半死,汗水和泪水滚烫地流着,心里忽然幻想这世间有没有灵丹妙药,把老爹的麻烦一次性祛除。
还是熟人照顾,父亲总算进了病房,有了病床。我和母亲每天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老婆那边又来电话,孩子总是发烧不退,说要我不告诉老人家,但父亲耳朵尖,听到了,在床上急得哆嗦。
这家医院的医生极其负责,每天查病房问得很仔细,虽然脾气暴躁,不对头就把病人家属甚至病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我也认了,只要他们认真负责。起码父亲进医院才两天,他们就查出了病情,不像在广州一直耗着,痛着。
想着要不要送红包,手里拽着一千块钱,在医生办公室外等着,却怎么也出不了手,医生身边总是挤满了人,插针也得有根缝,这里连缝都没有。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是你手里拽着红包,要送的对象就在咫尺间,却怎么也送不出去。
主治医生没送红包,麻醉师也没送红包,我总疑心给父亲找了最差的医生,动了最差的手术,得到最坏的结果。
而一位同学说,他老妈生病动手术,因为兄弟姐妹多,大家商量着,办法就多了,红包也送了,也请医生吃饭了,手术也满意,听得我惭愧加惭愧也。
在老人家关键时刻,能商量问题的,最好是兄弟姐妹。偏偏我是独生子,父亲则是独子,两代人都没得商量。
当然,自己无能,也不能怪没有兄弟姐妹。
父亲动完手术,切了一个肾,因为病已经走到肾脏。家属去手术室领人,护士只负责带路安排,不负责运送。
我和母亲走到手术室旁边一间大房间,但见阴风嗖嗖,阴气沉沉,一大群术后的病人躺在那里,一个个牙关和双目都紧闭,神色惨淡,都是鬼门关闯过来的。
一床床带轮子的病床纵横摆列,老爹在何处?满屋子找老爹,护士很严肃地说:“找到亲人,就要喊,喊醒来,不然就睡过去和你们永别了。”这不是喊魂吗?
在一大堆人当中找到老爹,他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如同死去,我和老娘吓坏了,一路推车,一路喊,喊他游荡的魂。
从手术楼回住院部,端的不易也,好一道斜坡,运过去时,是下坡,怕病床下滑过快,把病人抛下来;运回来时,又变成上坡,拉得好吃劲,好似在跟死神比赛似的。
父亲躺着,没有反应。
有一位农民大哥,和我们同县的,虽然人瘦,力气却大,他老婆运气奇差,患肾癌,这据说是十万分之一的比例。他先把老婆的车推上去,看我们吃力,走过来,一手猛力一拽,父亲的病床就飞翔一般上了坡。
后来我跟他聊,他说:不晓得老婆吃了甚么东西,得这么个病。现在想起来,幸好没有听政府的号召,而是和政府对着干,拆屋子也好,牵耕牛也好,把谷子挑走也好,他就是要生崽,结果生了三个闺女,虽然未达成心愿,但还是尝到甜头。这回老婆生病,家里的事情全由三个闺女管,自己放放心心地管老婆。
说到这里,他吐了一大口烟,露出熏黄的牙齿,得意地笑:“幸亏生了三个,三个好闺女。”一种抗争之后胜利的笑容。
和父亲同病房的是湖南师大的保卫科干部,六十来岁,复员军人,老婆是省政府的,只有一个儿子,八零后,当时考上了香港大学,学的导演专业。
我每天跑上跑下,那位阿姨看在眼里,忽然责备我爸妈说:“你们两口子怎么只生一个呢?你儿子好可怜呢,我都心疼他好久了。”
其实我当时没觉得自己多惨,她这么一强调,我倒真的觉得自己够惨。
这话不知怎么地就传出去了,那些只有一个子女的家长都过来看望父亲,都过来同情我,然后大家都叹息,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将来叹息: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老了怎么办,孩子将来负担重怎么办?
我成反面教材了。
小时候父母单位同事那些艳羡的目光,此刻都消失远去,模糊在地平线上,而取之而来的是冷酷的现实,焦灼的现实。
我那时确实很焦灼,一种单兵作战的焦灼和惶恐。本来吗,为人儿女,照顾父母,天经地义,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个兄弟姐妹,确实要好过一点。
没有过长夜浩叹,不足以谈论人生。
我想我是有资格谈人生了。
我那时候,就常常地长夜浩叹,感叹没有兄弟姐妹。这种感叹,在老爹第二次动完手术尤其强烈。
老爹第二次从鬼门关回来,身体就从来没有清爽过,疼痛感一直不消停,起初用理疗机还可以应付一阵,后来理疗机也不管用,直接用吗啡。隔三差五地住院,母亲每次都得在医院陪通宵,父亲痛,母亲就没法睡,帮他按摩。
县医院条件差,晚间保暖措施不佳,一到傍晚,父亲就催母亲回去,说:你不能陪我睡这里,晚间感冒,你若病了,儿子又远在广州,那就两个老人等着完蛋,你赶紧回去。
于是,母亲每到傍晚,就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去,看到别人一家子团团圆圆健健康康跳舞,上馆子,心酸得直落泪。
我在广州,也没几天开心日子,有时候和同事开玩笑,正要开怀大笑,一想到当天打电话回去问父亲的病情,母亲总是说父亲还在痛,就实在没有笑的心情。
我和老婆都得上班,孩子怎么办?把岳父岳母请过来,结果过来没几天,他们的孙女又病了,老两口火急火燎地回湖南,没了老人,我只好带着儿子去上班,安置在办公室。
记得有一回带着儿子去单位食堂吃中饭,儿子闹着要吃汤粉,我把他抱在胸前,去汤锅前,同事们惊叫起来:“你也不怕热汤溅到孩子身上吗?”
居然狼狈至于斯!
这种情况实在没法维持,父亲在湖南着急起来,要把我母亲赶到广州来,母亲说:我去广州照顾孙儿,你老头子咋办?父亲骂起来:我是个没用的人了,你管我做甚么?快去管我的孙宝,求你了。
母亲一把眼泪地南下广州,当时是隔壁的简师母陪过来的,刚到广州,简师母家里就传来坏消息,说他儿媳妇腰疼,后来查出是肾癌,又是十万分之一的概率,真是扯淡,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家乡,咋就这么多病!
母亲一头挂念着老爹,一头管着孙,那时候父亲自己挣扎着去医院化疗,是母亲的朋友们帮着送饭。
我也焦虑着,经常梦见孩子不见了,找不着了,或者受伤了,梦里急得哭。
有一回梦见儿子的摇篮居然放在窗户外面,高高地挂在八楼的外空间,儿子就这么高空睡着,我急得捶胸顿足,责备母亲和老婆,梦里头嗓子都喊破了。
父亲在湖南病痛得实在不行,母亲只能扔下这一头的孙儿,回湖南照顾父亲,而岳父岳母得在家乡看管生病的孙女,这人手挪来挪去,总觉得不够用,总觉得多一双手就好了。老天爷,从哪里增一双手呢?又不能临时制造。
当时先请了老婆的堂侄女当保姆,不久,岳母又抛开她的孙女,让岳父在家乡照顾,自己来广州给我们带小孩。
老天爷似乎专门挑倒霉的人下手,这么挪来挪去总算人手均衡了,结果岳母身体不适,发现是子宫癌!只得回家治病。好在老婆还有弟弟,岳母治病动手术全靠他照料,如果老婆也是独生子女,想一想都冒冷汗。
到2009年暑期,父亲几乎已经离不开医院了,每天晚上都巨痛,母亲则一天到晚没法合眼睡觉,从家里跑医院,从医院跑家里,做饭做菜,送饭送菜,穿梭往来,疲于奔命。
可怜老爹老娘,两条老命,一个为病,一个为照顾病人,就这么惨烈地耗着。
父母山穷水尽,我必须得回家了,休年假也好,请事假也好,扣钱也好,没薪水发也好,我都得回去了。
感谢老婆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业,正好是暑假,她起码能全身心照顾孩子了,我没了这层包袱,总算可以放心回湖南。
当时的老爸,只有三十多公斤了,一身的骨头,触摸着都手痛,心更痛,母亲也瘦得叫人揪心,满头白发如飞蓬,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如同癫婆子一般。
那时岳母已病入膏肓,幸亏有小舅子照顾着,父亲已离死不远,但他在总是安慰愁眉苦脸的我,反复用抱歉的语调说:“儿子,辛苦你了,等我病好了,一定到广州去给你带孩子,解除你的后顾之忧。”
我回去之后,其实并未减缓母亲的辛劳,老婆带孩子,煮饭菜,母亲送饭菜,我陪父亲,但也不能从早陪到晚,还是得和母亲轮流看护。就是说,母亲也要和我轮流熬夜看护父亲,因为实在找不出第三个人来。
与父亲同病房的是一位老教师,姓凌,女儿居然是我同学,那时的校花,如今的县地震局局长。儿女成群,且都孝顺,每天自朝至夕,轮流陪护,人手之多,每天居然不用重复,我那位女同学可以两天来一次。
而同病房凌老师的老伴,有了儿女分忧,就不像我老娘那么遭罪,连饭菜都不用送,白天陪着老头子坐一坐聊一聊就可以了。
人多,力量果然大。
真不明白,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爱宣传人多是负担,连万恶不赦的张春桥都说过:人不是负担,人有脑子有手脚,能给社会创造财富,能生产,怎么是负担呢?
作为县委退休干部的姑父,也很生气,有一次敲着桌子说:侄儿,你去找人民政府,要政府派看护人,既然你爷娘响应号召只生一个,那么政府就得负责任,照料你的老爹,而不是让你这样狼狈不堪。
都是些废话,气话,老爹病着,又不是政府病着。
当然,如果政府病了,我是不会去当孝子的,去***的蛋。
父亲一到晚间就剧痛,剧痛就打吗啡,打完之后就发烧,翻来覆去,需要亲人肢体上的抚摸,但母亲累得连抚摸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时候我终于感性地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合不合理,不在于人口多少,而在于青壮年在人口中占的比例,比例大,社会就充满生机。
我感叹没有兄弟姐妹,有人可能会反驳:儿女多有什么用,如果都不孝顺,不如不生。
这话在理,也不在理,儿女多未必是好事,但如果社会上年轻人不多,那肯定不是好事。年轻人就是社会的儿女,是全体老人共同的儿女,把范围一扩大,问题就明晰了。
有一个很傻逼的说法:老人不靠儿女养老,靠政府养老。
政府公益服务行业是由什么组成的?还不是由人组成的?主要是由年轻人组成的!现在的退休金从哪里来,真以为是你年轻时候积攒的?非也!是从现在的年轻人中年人的手里抽出来的。社会上青壮年不够,谁来保证生产,谁来保证养老?
人手,重要的是人手。如果把我的家庭放大,放大成一个社会,这个道理就更明白了。我的家庭人手不够,放大成一个社会,就是劳动力严重不够。
大道理不说了,还是说老爹的事。
陪了父亲半个月,又得想着上班的事,但担子全部落在母亲身上是很残忍的,老婆也得管一管岳母的事,没有弟弟妹妹来顶,只好请护理工。
护理工是个中年妇女,我拼命地给她钱,求她多照管我老爹,她也拼命地答应。恰巧那时父亲的疼痛嘎然截止,浑身轻松下来,胃口也好了,我和老娘很专业地高兴起来,以为老人家又可以活一段长时间。
我居然忘记了一个成语,一个叫“回光返照”的成语。看影视上的老人回光返照,我们清醒得很,轮到自己父亲回光返照,我们却盲目了。
毕竟是自己的亲人,总会抱着良好的预期吧。
父亲也觉得自己好了,于是催着我回广州上班,不能再耽误了,我也高兴地说:爷,再过十来天是你生日,我先积攒几天假,到时候可以回来给你做72岁的寿辰。
一家人都相信这个预期,于是我决定暂时回去上班。
那天,走出病房,不忍,又回过来看老爹,握着他的手,老爹不耐烦地说:回去吧,回去上班。
我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瘦骨嶙峋地侧卧着,面对墙壁,不由得眼泪刷刷地流,心里直疼,想着一定要给他好好策划一个生日,让他高高兴兴度完最后一个生日。
没想到,一走就是永别,生日的蛋糕只能烧给他了。
不到两天,父亲就在无人知晓中走了,不痛不挣扎地走了,请来的护工拿了我那么多钱,居然推说要去洗澡,离开病房回家,母亲当时在家做饭,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走了,具体时间不详。
对于护工而言,反正又不是她老爹,什么时候死的,关她什么事。
如果当时是弟妹守着,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这么一个看重送终的国度,我的罪行大了。
我去父亲住过的病房喊魂,叫声爷老倌,你跟我回去吧,这里不是你睡的地方。
心里痛恨得自己不行,又幻想着如果有个弟妹,暂时替我陪护父亲几天也好,弟妹可以告诉我,父亲走的时候怎么样,说过什么话,有什么表情,对我有什么话要说……
父亲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希望那一阵寂静是安详的,而不是在无人陪伴中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生日,他来了,来到我梦里,一身清爽,穿青衣,高兴地说,我的身体都换过了,原来的病体扔了,好舒服。
如果,父亲是活着说这句话,该多好啊。
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说是吗?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