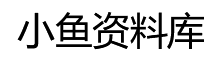《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4000字
在念书的时候,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要远远超过托尔斯泰。这种偏爱可能仅仅是因为,出于偶然,我先接触了《罪与罚》,然后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那时,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由衷地敬佩,认为他代表了人类心灵的深度,这当然要比代表了人类心灵的广度的托尔斯泰来得厉害,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真正读过托尔斯泰的任何作品,只是凭借一些浮光掠影的二手印象,认定托尔斯泰不过是一个推崇人道主义的老好人,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对历史和人性黑暗面的无知,意味着浅薄。
直到2022年底,我大病初愈,渴望摆脱那种绝望的,被各种阴险设想、死亡意象追踪的状态,几乎是在命运推动下,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复活》。并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与陪伴下,真正康复起来。
当然,我不会因为个人经历,再犯一次年轻时候犯过的错误,武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谁优谁劣。我在心灵壮健的时候,倾向于《罪与罚》;而在心灵衰弱的时候,倾向于《复活》,这种倾向能不能推广到两位伟大作家的所有作品,是不是适用于所有读者,我不知道。
前不久,志军兄在豆瓣上发了一条《复活》的短评,他说:“从头到尾笼罩在一种强大的善的观念的阴影之下,所以有一种至善特有的乏味。再加上这个时期托尔斯泰关注比较多的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宗教,写那种劝人从善的故事的比较简单文风也让这书打了些折扣。”他说这番话,是以《安娜·卡列尼娜》为参照对象,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
现在,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我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同意志军兄的话。
并且,也是通过志军兄在豆瓣读书的标记,我才知道托尔斯泰的女儿亚·托尔斯泰娅所写的《父亲---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这本书,中文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译者是启篁、贾民、锷权。
结合这本“传记”,以及《安娜》一书中显然带有托尔斯泰自传色彩的“列文”这个角色,我觉得我对托尔斯泰有了更多了解。
一个拥有精神生活的人,会依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生活处境,倾向于求真、求善、求美这三条不同的道路------尽管人们常说,这三条路殊途同归。这三条路各自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哲学家与科学家是求真者的代表,宗教人士是求善者的代表,艺术家则是求美者的代表。那些认识到这三条路,其实通往同一个方向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真正的求美者,比如说一个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及其围绕整个创作构建起来的生活当中,是不可能不触及到真与善,并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方法来运用的。
而托尔斯泰是一个毕生的求善者,始终如一。这并不是说他毫不考虑美和真的实现,但他确实并不以美和真为最高人生目的。他以善为宗旨,在对善的追求过程中,实现了美和真,仿佛后者只不过是附带现象或意外产物。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和真是其求善的方法,就好像古代少女为了寄托情思,将心力全部投注到一个荷包的刺绣上面那样。绣荷包当然是为了有朝一日寄予情郎,乃至最终结两姓之好,但少女在专心劳动时,并不会为自己设定嫁作人妇这样的具体目标,如果这么想,就会粗鲁、俗气,而且荷包也绣不好。
在《安娜》中,托尔斯泰借书中角色之口说,他拒绝左拉那种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也很难从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谢林那里获得真正的教益,这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求真者:既不像左拉那样通过文学来求真,也不像黑格尔那样通过哲学来求真。他心仪的对象,按照托尔斯泰娅的介绍看,是卢梭。而卢梭是一个对艺术与科学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就是对美和真的价值,有所怀疑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精神聚落来定义这个“群”,可能比行当、职业等名目,更方便我们进入我们想要了解的人物的内心。比如说,同为文学家,托尔斯泰是求善者,屠格涅夫则是求美者。求美者,以《会饮》里的阿伽通为典型,其特征是厌恶暴力,心肠柔软,逃避人世间的黑暗。求美者对求善的政治与宗教领域感到隔膜,容易对道德持鄙夷态度。至于求真者,可以举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为例,现代从事逻辑学、分析哲学或实证史学研究的学者,亦属此列。无论是以传统伦理,还是自由主义伦理引导自己的人,都是广义的求善者,这意味着求善者类别并非求善者阵营,同一类别的求善者,也许分属不同阵营,彼此之间的斗争可能与求善者与求真者之间的斗争一样惨烈。
我之所以采用真善美这样老掉牙的概念,来思考我所遇到的古人和今人,是因为借助这些概念,似乎能把握到某些统一性。比如,我认为孔子是求善者,将目光从天上投向城邦的苏格拉底也是求善者,柏拉图是貌似求真的求善者,亚里士多德则是貌似求善的求真者。而当代中国学者,就我所熟悉的,研究法学、政治哲学和古典学的,大都是求善者。尽管很多学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挥舞着科学的旗号,貌似求真者,但在根柢上,他们仍是求善者,只不过所信奉的善的原则彼此不同。
受制于形形色色的ism,他们之间的冲突,在根本上是善与善的冲突,他们处理这种冲突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一,将对方贬低为恶,于是善与善的冲突,就成了善与恶的斗争。这是一种最幼稚的方法,近乎孩子气的划分敌友,但同时也最容易被采纳,最为人们所习惯;二,将对方吸纳进自己的体系。近年来流行的“通三统”的思想谋划即属此列。这种方法在根本上,是一种“礼”的构想,以否定、批判、但绝非消灭的态度,将对方保持在思想内部。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比第一种方法更明智,更审慎,而且也开辟了通向真的可能性。如果说将对手宣布为恶而予以摈弃,在思想上容易流于狂热和懒惰,那么构想一种思想的“礼”的秩序,则要求更深入地理解对手,要求更冷静、更富有同情心,尽管这种方法不可能否定自身的主体性,所以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不是思想态度。三,否认自己是求善者,将自己打扮成求真者,同时指出对方是求善者,是无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触及科学的层次的乡愿。
用真善美的分类法,来观察当代思想人物与事件,会更容易看清一些脉络。例如,我认为刘小枫就是一名求善者,从《记恋冬妮娅》到“国父论”,其求善的旨趣一以贯之。在青年时期,他还会被美魅惑,但在领受自己天命的过程中,越来越摈弃身上的文学青年气质,其标志是写出那篇嘲讽阿伽通的文章。因为如果不抛弃文青气质,则不能彻底打开进入政治思考空间的渠道。不过,刘小枫对政治的理解,是纯然古典式的,或说伦理的,他既从善恶角度来理解政治,也从善恶角度来理解宗教,也从善恶角度来理解哲学。但他对善恶的思考,永远固守常识的层次,不愿意从中抽象出伦理学。这一点,他与他求真意志更旺盛的思想晚辈,如李猛和吴飞,是很不同的。
在晚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他越来越多带有文明本位色彩的观点,使他更像是古希腊城邦的诗人,而非哲人。如果说诗人是城邦显见的捍卫者,哲人是城邦潜在的颠覆者,那么,在对苏格拉底问题进行了通盘思考,意识到哲人角色,在当代中国既不利于开展教化,也不利于自保之后,倾向于做一个诗人,当然是他的自然选择。
而以为他称毛泽东是“国父”,就是彻底倒向左派的看法,显然也是短视的。他对待1949政权的基本观点是,毛的种种错误与现代中国的种种灾难,都要归咎于现代启蒙,而不是归咎于自由主义者认为的启蒙不够。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尚未厘清的矛盾:他曾极力否定顾彬将现代中国革命归因于基督教影响的做法,梳理出《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我们不知道,如果毛的现代革命与儒家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代革命显然又是现代启蒙的伴随现象,那么毛的种种错误与现代中国的种种灾难,是不是需要儒家部分负责?
做为一个自始至终的求善者,刘小枫究竟是效仿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区分,隐藏了自己求真的一面;抑或是他本性就容易“信以为真”?今天又读到他一篇最新文章,《东亚史的新与旧》,其中的思考和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指出看似求真的实证史学,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是求善(求恶)的意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政治领域的善,始终有其局限性,局限于一个城邦,一个国家。冈田英弘和宫崎市定是日本学者,当然是力求实现日本的国家意志,追求日本人的善;而中国学者则会力求实现中国的国家意志,追求中国人的善。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各自的求善意志,都是无可非议的,哪怕双方均视对方的求善意志为邪恶,也不影响这种相对的善的存在。如果要发出真正有力量的批判声音,则需要超越政治,超越国家,寻找到一条中日两国均奉行的文明准则,如此才能实现有效的批判。但在《东亚史的新与旧》中,看不到刘小枫有这样的努力,只是纠缠在日本人为汪精卫翻案,或我们不应该接受日本史学洗脑的詈骂上。
可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自己的主体性,自己的善,去拥抱敌人的主体性,敌人的善。日本的东亚史研究,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之所以会吸引大量拥趸,并不是人们心甘情愿地缴械投降,自愿交出了自己的求善意志,而是因为,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都披露了大量的历史之真,这是难于反驳的。我们只有写出包含同等分量的历史之真的著作,才算是荷枪实弹地与对手交战,否则我们的意志所求来的善,在对方披露的历史之真的映照下,就会显得虚伪,变成伪善。况且,在当代总体性的科学视野之下,求真本身,就意味着实现一种在知识领域成就善的生活,所以会形成跨国跨文明的学术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拥有不同国家公民身份的学者,真诚地交付出自己的主体性。固守自己的国家与文明意识,只会堵塞和削弱这种新的可能。
最后想说的是,目前尚看不见任何端倪的,只存在于一些学者好心的想象中的东亚共同体,能否成为现实,也许并不取决于思想如何攻守,而要取决于物质的合作与发展。我记得刘小枫曾奇怪地大力推崇科耶夫,赞其为“欧盟之父”,但根据翻译过来的《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来看,现实的欧盟的成立,与科耶夫原初的设想,相距甚远。现实的欧盟起源于德法两国的煤钢共同体,纯然是一笔经济账,而科耶夫盘算的却是一个以法兰西为主导,以意大利、西班牙为拱卫的天主教世界。科耶夫心目中提防的敌人新教德国,最后反而是法国最忠实的朋友。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讥讽知识分子的空疏、无用、妄想,因为世间一切事情的落实,都不会百分之百如人所愿。但是,如果我们的教师,希望我们捍卫自己的国家与文明,是应该教导我们停留在政治的,你死我活的,敌友之争的层面思考,还是应该教导我们努力超越政治的层次呢?(吕翔)
相关文章: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