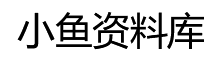苏轼传读后感
东坡的一生极复杂又既简单。说复杂指其仕途上几番沉浮,任职多地;思想上儒释道兼而有之,互生互补。说简单是因为,读其生平与作品,苏轼给你的感觉始终如一,即一个元气淋漓,思想与情感丰富,才华横溢而能永葆赤子之心的真人。
关于苏子的文章多矣,这些文章大都关注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几年的生平和诗文。此时是元丰三年到元丰七年,苏轼是45到49岁,正处壮年,处于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成熟期,仕途的坎坷造成思想情感的波澜起伏,酝酿出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彪炳千古的华章。读这一时期的诗文时,你能感受到一种属于壮年的气息。虽然乌台诗案中,苏子被“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在囚禁了整整130后贬到黄州任一闲置,但我们仍能从其作品中读出一种浩然之气,这种豪气是只属于这一阶段的。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赤壁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样的旷达,读来让人心胸为之开阔。这也大致代表了这位旷世奇才在人们心中的主要形象。
但我这次读其传记,对其第二次被贬谪后的诗文却尤其印象深刻。这一阶段的诗文少了些豪气,而更了些逸气。不仅行文自然巧妙,文本天成,少了些前一阶段的雕琢与修饰;而且思想上更加富于哲理与禅机,发人深省。东坡在给子侄的信中写道:“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周紫芝《竹坡诗话》)如果说黄州时期的作品是“气象峥嵘,五色绚烂”,那么惠州儋州时期的作品则称得上“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了,这其实是文章的更高境。孙过庭论书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学书如此,其实为文也这样,绚烂之后的平和冲淡,真正代表了人文俱老的最高境界。
来看看这一时期苏轼的处境和作品吧。
元祐八年(1093),苏轼,身至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下任宰相的最佳人选,正是“冠盖满京华”的时期。然而高太后去世,政坛巨变,于是绍圣元年(1094),苏轼千里迢迢奔赴贬所(英州),一路上朝廷五改谪命,最终贬到惠州。
此时的苏轼已是59岁的老人,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已于去年去世,身边只有小儿苏过,和侍妾朝云。白须潇散谪岭海之际,其心境可想而知,也正因此其诗文中流露出的哲思是那么真切动人。
贬往惠州路上,过大庾岭时,他写道: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没有悲伤,没有哀怨,一切的辱与荣,垢与净,执迷与觉悟仿佛都在大庾岭上分开,此时的东坡居士已将过去的所有尘世染污抛下,等待的是仙人为之抚顶,助其修道成功。
于是经过曹溪南华寺时他写道: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他认为自己本事修行之人,只不过因中途一念之失,误落尘网中,遭受了这么多年的坎坷。可见此时的佛老思想成为了其意识的主导。
绍圣元年十月抵达惠州贬所时感叹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这难道是梦中吗?我以前仿佛到过这个地方。这真是太富禅机了,《红楼梦》中的宝玉第一次见到林妹妹就说,这个妹妹我以前见过。正所谓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宝玉之语和东坡之诗,真是灵性之人的睿智之语。
东坡惠州的诗文,正是借助佛老思想,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脱:
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提刑》)
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与参寥书》)
此时的文章真的是妙手偶得,自然天成,臻于化境。随意的一篇游记,给人无限启迪: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记游松风亭》)
这已不是早期的五色绚烂,流光溢彩,思想上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豪气与执念;而是一任天成,平和冲淡而哲思深宏。就连一次小小的搬家,随笔写来也能发人深省:
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佑寺松风亭。杖屦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岭南岭北,亦何异此?(《题嘉祐寺壁》)
他认为身处高位和谪居岭南就像搬家一样,一处有一处的妙处,一处有一处的局限,这样看来,便可随遇而安了。
果然,稍后来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儋州,他也能怡然处之。此时,他已能够将老庄与佛家的思想出神入化的运用了,可谓用一生之浮沉阐释了释道之哲学:
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人生的局限无处无境不在,如此观之,一切便可释然了。这种文字置于《庄子》三十三篇中,也别无二致了。
谪居儋州之际,朝云已经去世,身边的亲人只有苏过一个,积蓄已基本花光,而自然环境险恶。而这位精神的富翁,却能用自己的达观,将如此贬谪之地,变为乐土。并写出《谪居三适》这样平易而富于哲思的诗作。
兹录其一:
旦起理发
安眠海自运,浩浩潮黄宫。
日出露未晞,郁郁蒙霜松。
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
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
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
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
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
琱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
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
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
早起梳头百下,是苏轼坚持一生的习惯,以此养生能“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在这贫瘠险恶的海岛之上,如此平凡的生活细节竟成了丰厚的精神享受。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那个“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东坡居士,而纯然是一位饱尝甘苦归于平和的老人,于日常细节中品出人生真谛。于是他感叹,年少时嗜睡,但为了上朝总不免匆匆早起,只能随便搔几下头发,还要佩戴重重的冠巾。现在想来与驾辕之马没什么不同,都是满头风尘,身上佩戴的玉饰发出的声音,实在和犯人身上刑具发出的声音一样。
至此,苏轼还是那个苏轼。但已从当年的豪放旷达,变为睿智通脱;由流光溢彩,变为平淡冲和;由辞采华茂,变为浑然天成了。(耿世涛)
相关文章: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