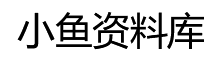唯美古风诗句赏析
由月及人,于是有“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里有一处古今语义的差异:所谓“情人”,好友也是情人。唐人送别吟诗,如果送的是一位~情人”,其实往往是送朋友,比如韦应物《送李二归楚州》的“,隋人南楚别,复咏在原诗”i再者,唐人说相善的乏力——读张九龄《咏燕》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面对现实的满目疮痍,我欣赏张九龄“无心与物竞”的超然与淡定,但我更敬重罗曼·罗兰“不管人生的赌博是得是损,只要该赌的肉尚剩一磅,我就会赌它”那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勇气。隐士们用激流勇退、置身事外的方式来坚持操守,表达拒绝同流合污的立场,我能够理解;但我偏激地以为,放弃斗争是对自己的鄙薄,对信仰的出卖,并不值得颂扬。
恶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善的缺失,而是因为善的乏力。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中国咏物诗的传统是言在物而意在物外,也就是指东打西,借物抒怀。这首诗表面是写燕子,实际上表达了张九龄自己的政治心态。海燕分明就是自己,鹰隼分明就是政敌。
一开篇就很用心思,“海燕何微眇”,重点在“微眇”两个字上,字面是说燕子身形很小,暗含的意思是说我只不过是个卑微的小角色;“乘春亦暂来”更有深意,所谓“乘春”,是说海燕的飞来与其说出自己的主观动机,不如说是得益于春光的拂照——张九龄家在岭南,在当时是文化很落后的地方,时代稍前的禅宗六祖慧能也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才在初见弘忍求道的时候为自己声辩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正是武则天着意打破门阀政治,给庶族读书人入仕做官的机会,张九龄才有可能以寒微之身官居高位,所以他可以说是武后新政的受益者,所以才有“乘春”之语,而“暂来”二字更暗示了自己不是恋栈权位的人。
接下来的两联,都在加深首联的意思,重点则在尾联“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庄子》有一段著名的故事,说惠施在魏国为相,听说庄子也要到魏国来,非常紧张,生怕被庄子抢走了自己的相位,于是派出人手四处搜查。庄子于是找到惠施,讲了一个比喻“有一种凤鸟,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抓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看到凤乌飞来,以为它要抢走自己的老鼠,便仰头大叫,想要吓走凤鸟。如今你惠施也和猫头鹰有一样的担心鸣?”《庄子》的这个故事常被称引,比如李商隐就写过“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其实这反映的正是人类一种固有的心理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以己度人,尤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把这个意思写在诗里,李商隐的写法就很直接,明显对自己的敌人很不屑,而张九龄是个政治人物,话说得就很委婉,没有把自己比作清高的凤鸟,反而比作卑微的海燕,说泥巴里栖身的海燕之所以偶尔飞进华堂,只是春光造化使然,它自己绝对没有任何的争竞之心,鹰隼之类的大鸟实在犯不上猜忌自己。
尤袤的《全唐诗话》记述过这首诗背后的故事:那正是著名的大奸臣李林甫崭露头角的时期,张九龄的宰相位子越坐越不安稳。在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问题上,张九龄大大地触怒了唐玄宗,李林甫抓住了这个机会,屡进谗言,说张九龄心怀怨谤。现代读者恐怕不易理解:对皇帝心怀不满,看上去无非是心里的一点情绪而已,又不是实际犯了什么过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但在专制政治下,这可是极大的一条罪过,人生是个苍凉的手势——读王维《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往往,行到水穷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选择坐看云起——对这复杂的句子作一次精简来帮助理解,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选择”:再删去不必要的修饰,只留下主谓宾,是的,是“我们没有选择”。很多时候,豁达都不是一种你可以信手拈来,也可以恣意淘汰的选择。更多的时候,那是现实留给你的唯一出口。
豁达是穷途末路时对命运最后一次视死如归的反抗。
王维工诗善画,素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又笃信佛教,亦官亦隐,画画得清空,诗写得恬淡,好像是彻悟大道、逍遥自在的,但实际情况远比表面现象复杂得多。
这首《终南别业》写的是王维信佛的一面、隐逸的一面、恬淡的一面,但他的隐逸和传统佛教是大不一样的。单从诗题上看,所谓“终南别业”,是长安附近终南山的一处别墅,即辋川别墅,原本是属于宋之问的。古时候的别墅,没有联排,没有合院,都是独栋,也都坐落在远离尘嚣的地方,享受着无穷无尽的山清水秀。正如现在的香港有半山区,北京有号称“富人后花园”的西山,唐朝的终南山正是唐代长安达官显贵们的别墅专属之地。王维的官做到尚书右丞,品秩不可谓不高,享受这样一座别墅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王维自己并不用这个逻辑来思考问题,他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这是一个省略了关系副词的因果句,意思是“因为中岁颇好道,所以晚家南山陲”,卜居南山的原因不是享受,而是“好道”。这句话的措辞非常巧妙,给人的印象是:诗人因为“好道”,所以离开城市,僻居在南山脚下。这就要联系诗题才能知道:所谓僻居在南山脚下,住的既不是茅屋,也不是草堂,而是一座豪华别墅。
这和“好道”似乎很矛盾,但这个矛盾早已被人巧妙地弥合了。先要解释一下这里的“道”字,这并不是指道家或道教,而是指佛教,这是有一番历史渊源的.佛教在东汉时期初传中土,而东汉正是一个谶纬盛行、鬼神遍地的朝代,时人是把佛教归入道术的,这个道术的意思不是道家之术,而近乎于方术,学佛叫做学道,就连《四十二章经》里佛门自己都自称“释道”。及至魏晋,人们也常把佛与道一同列为道家,以和儒家相区别。
话本小说和评书里,和尚经常自称“贫僧”,其实和尚原本是自称“贫道”的,意思是不成器的修道之人,是个自谦之词,后来发现这个称谓实在容易和道士搞混,这才改称贫僧——僧这个字本来是表示四人以上的僧侣团体,是个集合名词,用来用去也就约定俗成了。《六祖坛经》里,慧能大师在大梵寺讲堂说法,座下有“僧尼、道俗一万余人”,这个“道俗”里的“道”就是在说和尚,意思是“修道之人”,所修的道自然就是佛家之道。
修佛本来是一件很清苦的事,至少以世俗眼光来看绝不舒服。在古代印度,出家不是指进入寺院过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生活,而是孤身一人抛弃一切,到森林里或者石头缝里找个地方进行苦修,所谓持戒也只是个人的事,没有外界约束,全凭个人毅力。
时间永在,是我们飞逝——读刘希夷《代悲白头吟》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
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娥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无论文艺鉴赏家们最终宣判“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反复是用来强调生命无常的高竿手段,还是无意义、浅陋的文字游戏,大多数的读者却被迫采取和诗人一样的节奏踏上通向生命真相的螺旋楼梯,持续下沉,直至触底:公子王孙,宛转娥眉,无人打破时间的牢。一切企图阻止时间飞逝的行为皆是徒劳,因为,时间永在,是我们飞逝。
刘希夷的这首诗通俗易懂,不烦解释,以至在诗人生活的那个以富丽雕琢为美的时代里(高宗朝)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主流审美观发生了变化,《正声集》适时出现,把它标举为“集中之最”,这才为它赢得了显赫的声誉。尤其是诗中的“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更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越来越被世人传为名句,一直影响到林黛玉那首更加凄美忧伤的《葬花吟》。
当林黛玉唱起《葬花吟》的时候,稍有一些敏感的人都会知道,吟唱者的命运已经在这首诗里被注定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样谶语一般的句子也是从刘希夷《f弋悲白头吟》的传奇遭遇而来的。
刘希夷是河南汝州人,和前文讲过的王勃等人一样,也是个早年得志的典型。他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考中了进士,时年仅仅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之后,刘希夷就像当时的许多同辈一样,开始了一段漫游的生涯。
唐代很有游学的传统,真正是字面意义上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尤其是士子在科举及第之后并不是立刻就有官做,而是有一段守选时间,他们往往会趁着这个难得的轻松时刻四处游历,增广见闻。但是,事情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单纯,因为这种游历活动和如今的背包族、驴友之类大不一样,不取偏远而取喧哗,大多集中到两个最繁华的地方,也就是唐朝的两大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所谓游历,主要是进行社交,结交达官显贵,寻找政治靠山,官场上最要紧的“站队”工作往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士子们写诗投卷,吹捧对方,也作自我吹捧。要想进入主流社会,这也实在是必要手段。
但刘希夷有点例外,不去长安和洛阳,而是由中原入蜀,而后泛舟三峡,取道江南,把世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抛弃世俗的人,终于也被世俗所抛弃。那正是武后夺权政治混乱的时期,游戏规则一下子复杂起来,就连一心进取、不惜苟合取容的人都未必能谋得一官半职,谁还不敢拆封的信——读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如若在这之上再添任意一字一句,诗就会死去,就在这危急的一刻,诗人静静搁笔。其实,诗人并没有停止,他用沉默继续说话。
这首诗之所以广为传诵,是因为它道出了所有在外多年的游子在回乡途中所特有的且喜且怯的心理。游子久居异乡,和家乡不通音信,当真有一天踏上归途的时候,离家乡越近,心中却越是忐忑:家乡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家人都还好吗?会不会发生了什么变故呢?亲朋好友如今都怎样了呢?……如果遇到了从家乡那边过来的人,想问却不敢问,生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会让自己难以承受。久别的家乡,就像一封写满你切切想要了解却不敢拆封的信。
的确,单独来看这首诗,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但如果本着知人论世的态度来看,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诗中所谓“岭外”,就是岭南,即五岭之南。五岭是南方的五座大山,分隔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中国古代习惯称广东、广西一带为荒蛮之地,就在宋之问的时代,一位家住岭南的青年远行向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求学,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猜獠,若为堪作佛。”至少从字面上看,显然是有地域歧视的。
这种地域歧视,就是因为五岭隔绝南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很难传播到岭南,造成了岭南地区文化和经济的落后。直到岭南人张九龄做了宰相,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岭南地区才逐步地得到开发,而那位岭南猜獠后来则成为禅宗赫赫有名的六祖慧能,反而把岭南文化传播向中原了。
所以,宋之问时代的五岭,不但是地理分界线,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分界线。
过岭向南,就是政治失势者的西伯利亚了。宋之问这次被贬岭南,从正义性上说,因为他谄附奸佞,结果随着奸佞的倒台而一并受到了惩处,属于罪有应得: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是他在政治队列里站到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的一边,张易之呼风唤雨的时候,宋之问也鸡犬升天,张易之倒台的时候,覆巢之下自然也无完卵。
宋之问被贬岭南,途经五岭之一的大庾岭的时候,写过一首很有名的《题大庾岭北驿》,所谓北驿,就是大庾岭北边的一座驿站,如果继续向南,下一个驿站就在大庾岭以南了.就属于岭南荒蛮之地了。这首诗说: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当时的人以为,北雁南飞,最南端就在大庾岭,不会更往南了。大庾岭以南是大雁都不去的地方,久居中原繁华之地的大才子宋之问如今却要迈出这一步了,只能恋恋不舍地叹息着“何日复归来”。而没过多久,他还真就回来了。
宋之问这次回来,并不是遇到了赦免,而是偷偷从贬所逃出来的。在《渡汉江》这首诗里,所谓“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是写在岭南的生活和感受,而接下来说母亲是一个叫做“温暖”的地方——读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保尔·艾吕雅在《公共的玫瑰》中说道:“男人只会变老不会成熟。”我相信,正是母亲的柔软怀抱和无限温柔,使幼稚成为男人终生不会失去的权利。
孟郊的这首《游子吟》可谓尽人皆知,语言通俗,不烦解释。但是,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说大家都误读了这首诗,因为诗中的“慈母”并不是现代语义中和“严父”对举的“慈母”,而是古代礼制中的一个专门称谓,是负责小孩子教养工作的保姆。
这个解释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儒家讲周代的礼制,引孔子的话说过:贵族男子外有师傅,内有慈母,这都是国君给指派的保育员兼家庭教师。慈母死了要不要服丧,这是“礼仪之邦”里一个严肃的问题。鲁昭公幼年丧母,是慈母把他带大的,等慈母去世了,鲁昭公很伤心,想为他服丧,但负责丧礼的官员劝谏说这么做不合古礼。
但是,用礼制中的“慈母”来解释《游子吟》里的“慈母”肯定是错的。一来唐诗里凡称“慈母”,都是和“严父”对举的那个“慈母”,和礼制概念无关;二来这首诗的题下明明有一句作者自注“迎母溧上作”,已经道出了写作的背景。——孟郊是个读书人,读书就要考科举,但他没有王勃、刘希夷、宋之问那样的聪慧和运气,所以一直熬到四十六岁才考中进士,到了五十岁上才担任了溧阳尉这样一个小官,但他的功夫全在诗上,处理不来公务,便只能领到一半的薪水。这首《游子吟》就是孟郊担任了溧阳尉之后,把母亲接来时作的。
人类的一些感情永远会得到歌颂,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母爱,但在细想之下我们会发现,受到歌颂的各种感情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的,超平常情的,需要极大的意志力才能做到的,比如舍生取义:另一类是普遍的,永恒的,属于人类的天性的,比如母爱。在做过这样一个分类之后,我们或许会觉得疑惑:天性既然并不需要极大的意志力,并不超平常情,难道也值得歌颂吗7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于是,为了给这样的歌颂以足够的理由,人们往往会抹杀母爱中的“天性”这个属性,把天性之爱解释为非关天性的“恩情”,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父母养育之恩”。但勤于思考的人总是有的,古代有孔融,现代有胡适,都掀起过“父母于子女无恩论”的论战,只赢得了大批大批的反对者。
在一些反对者眼里,母爱之所以是伟大的,因为它的确超平常情,这个常情就是人类的自私天性。但在近些年来,这个论调终于站不住脚了,因为人类,乃至生物界,被确凿地发现出利他主义也和利己主义一样,属于天性。所以,当人类,乃至动物,甚至微生物,作出一些利他主义的行为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它们)超出了常情,更不足以说明他们(它们)品行高尚。——读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这世界上有许多奇怪的加减法,比如想念和留白。想念,在心里加上一个人,单数变双数,却更寂寥——如果我从未在生命中加上这个人,我就不会因为想念一个人而变得如此孤独。留白,山水画减去画幅中段的笔墨,电影减去男女主角的对白,维纳斯减去双臂……意义的空白处延伸出分岔丰富的小路.向受众揭露无限的可能性,有人被引向命运交叉的城堡,有人被引向果壳中的宇宙,目的地不明。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他什么都不说,你被他引向了哪里?
唐代,诗歌之所以繁荣,有一个一点都不诗意的理由:神女泛瑶瑟,古祠严野亭。
楚云来泱漭,湘水助清泠。
妙指微幽契,繁声入杳冥。
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
调苦荆人怨,时遥帝子灵。
遗音如可赏,试奏为君听。
陈季写得凄凉而古雅,尤其是“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修辞尤其巧妙:新月本来就“白”,暮山本来就“青”,但一经诗人点染,原本平常的事物突然被赋予了新的不平常的解释,新月之白与暮山之青仿佛都由湘灵鼓瑟的音乐氛围渲染而来,是音乐泛出了如此清冷的颜色。
魏璀也答了这个题目,他写的是:瑶瑟多哀怨,朱弦且莫听。
扁舟三楚客,丛竹二妃灵。
淅沥闻馀响,依稀欲辨形。
柱间寒水碧,曲里暮山青。
良马悲衔草,游鱼思绕萍。
知音若相遇,终不滞南溟。
【悲观卡义的花朵是心的名胜】
【——读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离别使月光变得珍贵。月如砒霜,洒在离人心上.
开出悲观主义的花朵。月是夜的名胜,悲观主义的花朵是心的名胜。
王建有一首诗叫做《自伤》,追怀一生,不免自怨自艾、自嘲自叹:衰门海内几多人,满眼公卿总不亲。
四授官资元七品,再经婚娶尚单身。
图书亦为频移尽,兄弟还因数散贫。
独自在家常似客,黄昏哭向野田春。
诗中的句子,看上去全是违反逻辑的,全是不合常理的。明明“满眼公卿”,却“总不亲”:明明“四授官资”,却仍然不过七品;明明有不止一次的婚娶,却依然孤单一身:明明“独自在家”,却“常似客”。这样的生涯是如此的荒诞,但是,写在作品里是荒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仅仅是荒诞,而是悲剧了。一生陷在这样荒诞的悲剧中无法自拔,便也只有“黄昏哭向野田春”了。
美好的诗,为什么常常以哀伤为代价呢?
如果爱,请深爱——读薛涛《牡丹》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武则天酷爱牡丹,大雪天赏花心切,明知违背自然规律仍是下了圣旨“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第二天牡丹没开,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将其从长安贬到洛阳。武则天的爱,有点轰轰烈烈的味道,带着“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的干脆利索,她的世界只有两种方式——要么热烈,要么毁灭。薛涛对牡丹的心情,像初恋,像一根纤细而坚韧,由两股拧作的绳,一股叫缠绵,牵引她从白昼到夜深,日复一日自醉:一股叫悱恻,捆绑她从去春到今春,年复一年轮回。
武则天有两种选择,爱或不爱;薛涛也有两种选择,爱或深爱。
唐代的诗歌高手中,有几位让人惊才羡艳的女子,李冶、鱼玄机,各有一番传奇,而这些女子中的翘楚则非薛涛莫属。在今天的成都近郊,仍然留着薛涛的吟诗楼,纪念着这位传奇女子最后的那段时光。
相关文章: